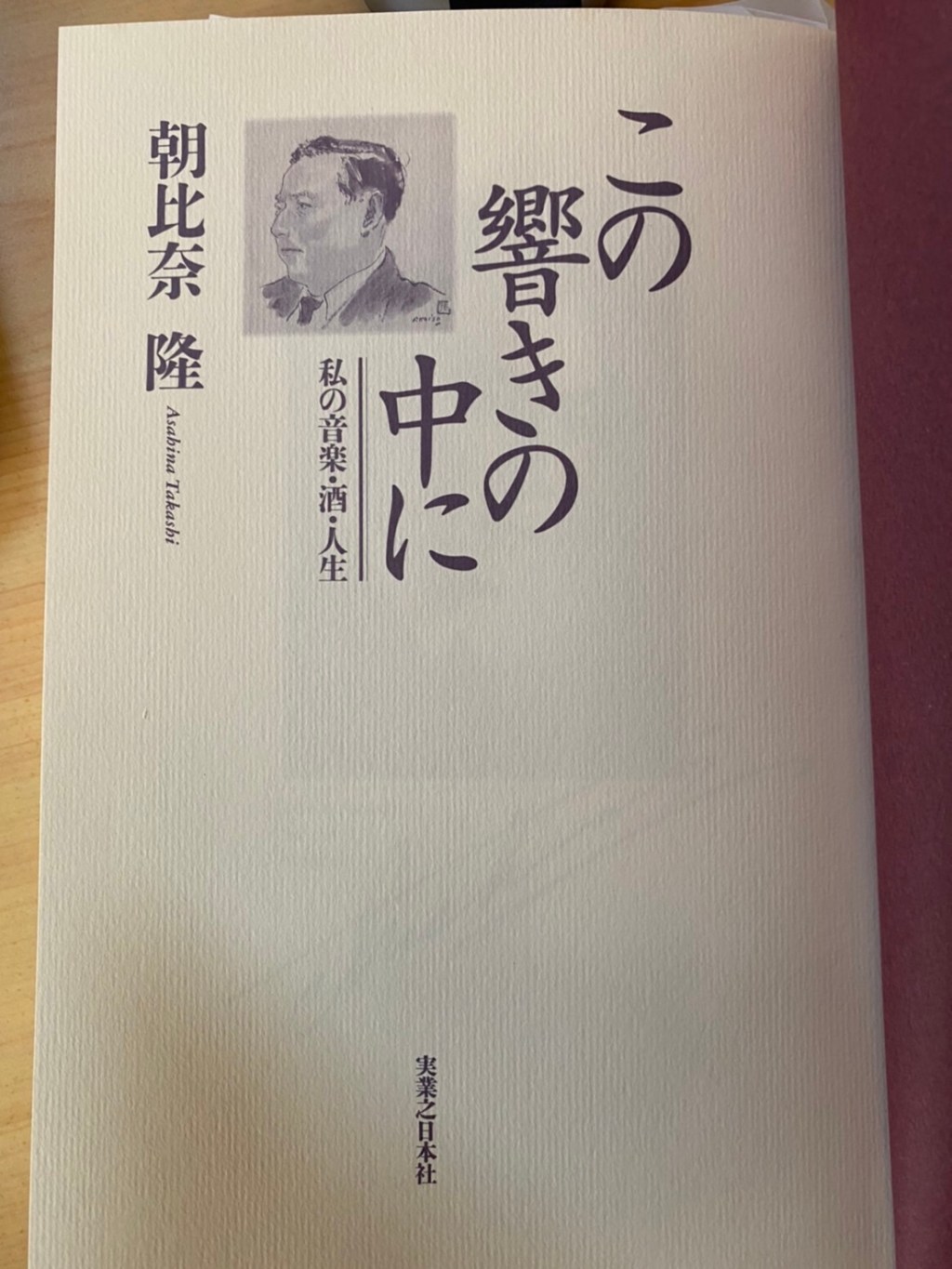這篇文章譯自朝比奈隆生前出版的隨筆集<この響きの中に 私の音楽・酒・人生>,其中的最後一篇文章<我が音楽人生の「到達点」>。
雖是講述他如何受到福特萬格勒「原典版」的啟發,領悟布魯克納、貝多芬、舒曼交響曲的演奏要領,但實際上是談19世紀末起因樂器進化,如何對演奏風格造成影響。
了解朝比奈隆的音樂軌跡,我想需要知道,朝比奈隆並沒有接受過正規音樂教育。1908年出生,高中時期朝比奈隆同時玩音樂、踢足球,大學進入京大法學部,以小提琴手身分跟俄國指揮家Emmanuel Leonievich Metter(1878-1941)學習音樂。大學畢業後先到鐵路公司上班三年,再回京大文學部攻讀哲學,同時在大學擔任講師,教授德語、英語、音樂史等課程(見朝比奈隆wikipedia),同時參與樂團小提琴演奏和指揮。戰爭期間到中國發展,主要在東北地區活動。戰後1947年成立大阪愛樂的前身關西交響樂團,此後擔任音樂總監一直到過世。
小提琴手出身、沒有留學歐洲、沒受過學院音樂教育,朝比奈隆花很長的時間摸索自己的音樂路。現在主要能買到奈比奈隆1970年以後的錄音,是這位指揮家已年過六十歷練出來的成果,風格上已相當穩定,但內涵仍會隨著每次演出變化。
文中提到的近衛秀麿(1898-1973)也是日本音樂界大指揮家,有興趣可以在youtube找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影片,包括在戰爭期間指揮柏林愛樂。其兄近衛文麿曾在戰爭期間擔任日本首相,日本戰敗後服毒自盡。
—(以下為譯文)—
死後的一百六十年,貝多芬九首交響曲是所有音樂學者、指揮家研究及論議的中心。從其出生到於維也納光榮死去,波瀾壯闊的生涯、來自富個性性格的許多小故事,以及幾乎概括所有類別的諸多作品,從具古典樣式的初期作品,到具暗示性及革新性的最後絃樂四重奏,其傳記、作品評論不記其數。由難解字蹟解讀及推敲而來的樂譜,進入本世紀雖然大抵決定性的出版已出現,但仍留下許問題,尤其對指揮家來說,其看似簡明的總譜,卻一而再再而三生出新的疑問。
此外,自十九世紀末以來,樂團演奏技術及樂器改良,隨之而起的規模擴大,迎來所謂黃金時代,林姆斯基・高沙可夫及馬勒作品所見豐麗的管絃樂法之進步,對貝多芬作品提出新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由大規模絃樂合奏認識到其音樂的巨大性,另一方面,由新的管絃樂法觀點看見其與管樂器群之間均衡的問題。
在與此平行的時代中,也進入了有能力且老練的大指揮家時代。管絃樂法也創造出甘美且豐麗的樂團美聲的魔法棒。學識、經驗豐富的指揮家,想使用魔法棒將偉大的貝多芬音樂變得更美、音響更飽滿,有如此想法是相當理所當然的。
管絃樂法將巴哈管風琴曲及樸素的斯拉夫民族舞曲變成大編製管絃樂曲,成就了雄偉的音響。
對青年時代的我來說,這樣的魔術還有著無限的魅力。我的老師Metter將短曲Trepac舞曲(譯註:可能是指胡桃鉗的"哥薩克民族舞曲")改編並以樂團試奏時,以及林姆斯基・高沙可夫<俄羅斯復活祭>中莫斯科大寺院敲擊的鐘聲,在不使用打擊樂卻演奏出美妙聲響時,給身為樂團小提琴樂手之一的我極大感動,難以忘懷。此外,我本身在師門下學習時,與其學習音樂的構成及和聲等等,更熱衷於學習管絃樂法之技術,這點我不得不承認。
大指揮家們在貝多芬、舒曼以及布魯克納簡樸的總譜面前,與其說心情受到驅使,將那有如黑白修飾的頁面塗成彩色,不如說這是使命、是義務,這點也能夠充分了解。
如此這般,可稱作貝多芬總譜「修補」的作業認真地展開了。當然,與其平行的舒曼及布魯克納也受其「恩惠」。
晚一個時代,於其後繼承的我們也跟著學習是理所當然,作為指揮家的要件之一,將「生於不幸」的此等作品以「近代進步技法」加以補強的技術成為了必要。
實例不止於此。
布魯克納的很多作品,於其在世時由優秀的友人及弟子們作成新「版本」,今天仍然可取得這些印刷總譜,也存在這些版本的錄音。也有些是作曲者本身「加工」的版本。這些都有「更優美、更豐富」的聲響。
關於貝多芬和舒曼的例子,不必求諸國外,我可以舉出身邊的例子。
例子就是日本音樂界的大先進,也是我尊敬的大指揮家近衛秀麿的勞作。近衛秀麿以令人驚嘆的天性,年輕時對西歐音樂的深入理解及技法習得,順應歷史潮流,很早就開始這項「作業」。戰前昭和初期便已發表完成舒曼第三號交響曲、通稱「萊因」的修補,舒伯特「未完成」交響曲,我本身在近衛秀麿指揮下演奏,對其妥當的音樂流動驚嘆不已。
貝多芬交響曲全九首的「近衛改訂版」從第二次大戰後經由美國,從柏林回國起到最終完成,聽說到去世前都還在與Peters出版社進行製版出版事宜。
其中第九交響曲,現存由其本人指揮讀賣日本交響樂團的演奏錄音,第三號交響曲「英雄」在其去世後不久於東京文化會館舉行的追悼演會上,我得到機會指揮在京各樂團聯合樂團的演奏。不論是木管、銅管,在增加種別及數量下,得到優美的音色及豪壯的動態, 是傑出的勞作。
近衛秀麿年輕在德國學習時,是理查・史特勞斯、法蘭茲・史雷克(Franz Schreker)、福巴汀克(Engelbert Humperdinck)等人活躍的後期浪漫主義之花盛開的「美好時代」,近衛秀麿以其可稱為是天性的豐厚資質,徹頭徹尾地吸收了其花香。
近衛秀麿的演奏指揮也經常是浪漫香氣濃盛,流麗自由,而且經常是快節奏但不失韻律,特別對被賦予樂團座椅、當天參與演奏者來說,是難忘的音樂體驗。
美好時日已遠去,對於由後頭前往的我們,新時代來臨。
將十九世紀這樣大世紀天才們的作品,作為具有悠久生命的事物傳達給下個世代,應可說是新的風潮。這風潮其實相當早以前就已經感受到。也就是指揮家魏因嘉德納、托斯卡尼尼等人「忠於樂譜」的倡議。
會發生這看似相當再理所當然的事情,是直到當時,由於歌劇院主演歌手們的恣意,對指揮家正常劇場作業的進行造成妨礙、進而損害到作品價值,因為有太多的案例而對其做出反擊。到後來還發展到出現「新即物論」(Neue Sachlichkeit)一詞,實際上這些巨匠們的演奏例與著作等等,對於「演奏的技術性正確」確實起了作用。
話雖如此,魏因嘉德納宛如入門書的<貝多芬的交響曲>之中,也相當有個人的意見及偏好, 由木管樂器的增減來評估表現的變化等等,從此類的問題便可窺知。由於法國號及小號還是由自然泛音構成的樂器,其調性下五度及下七度的欠缺用什麼方法彌補,仍然有議論空間。
身為貝多芬的奉仕者,四十歲到五十多歲時,我也在時代洪潮中左顧右盼,無法從管絃樂法的美妙魅力中自我解放,貝多芬及舒曼的總譜上,表現出我昏迷的自己鉛筆註記,日復一日越塗越黑。
最初的機會,是意料之外關於布魯克樂交響曲的到來。
自1953年(昭和28年)秋天,我得到歐美一周視察的好機運,首先到法國、英國、德國旅行,途中偶然應邀到赫爾辛基客席指揮其交響樂團一晚後進入柏林,又在千載難逢的好運下,於柏林愛樂定期演奏會的主會場泰達尼亞宮,聆聽福特萬格勒指揮的布魯克納第四號交響曲,一兩天後於法蘭克福的旅館,早晨在大廳裡與福特萬格勒本人有短暫交談。回應他簡短的詢問,我回答回國後最初演奏會要演奏布魯克納第九號交響曲,在他一連串關於「版本」的發言,我疑惑的耳裡聽到他說「原典版(Original Fassung)」的聲音。
由於知識不足,在沒有任何意圖我只準備了列維(Ferdinand Loewe)版的譜,我馬上到樂譜店購買現在還放在書架上的Breitkopf出版社原典版總譜。一覽時衝擊之大,讓我茅塞頓開。
就這樣開啟了我布魯克納交響曲巡禮,與貝多芬的情況完全不同,完全是白紙的行腳,沒有任何迷惘,一個接著一個閱讀原典版總譜及分部譜,我的耳邊那句簡短話語「原典版」響徹不絕。
也許很幸運的是聽眾的耳朵也完全是白紙,而演奏家們沒有抱持任何疑念,對日本音樂界布魯克納的接受者全體來說也是很幸運的事。
至於貝多芬的情況以及舒曼交響曲還需要些許歲月。
首先在1956年及接連的56年我得到柏林愛樂客演機會,分別被要求以貝多芬「第四」及「第一」作主曲目,這兩首交響曲在「修補」問題上是問題最少的,由於樂團有相當正統演奏風格,得到相當好的演出評價,給了我相當大勇氣。
被認為是「小交響曲」的第四號、第一號,在這大管絃樂團全員列席,含休息時間和巴托克、雷史畢基的大規模作品夾在一起,作為最後演奏曲目還可以正確把握住,讓我很有自信。
就這樣,1977年到78年,不知是第幾次與大阪愛樂的貝多芬連演音樂會,當計劃做現場錄音時,經過多年的遲疑我終於下定決心。
首先我把被貼上很多塗改用貼紙的管藥器譜、被鉛筆作記表情所掩蓋的絃樂譜收進書庫,使用每次到萊比錫客演購入的私用全新譜。首先整理已經用到老舊的總譜。把經年累月迷惘與苦心的痕跡、鉛筆的字跡擦掉。一頁接著一頁,橡皮擦屑屑下,白色的紙面浮顯出來。每擦去一行,過去努力及經驗的記錄跟著消失,全部徒勞白費的寂寞感籠罩著我。
然而就在橡皮擦屑屑下現出姿態的貝多芬音樂,有如被解放一般栩栩如生,我彷彿看見它笑嘻嘻地等待演奏家的手指將其重生。
也是在那段時期,有一次和一個樂團做最初排練,當我說「銅管樂器照印刷譜演奏」,小號席上發出「萬歲」的聲音。從那時候到現在,現在到將來,我希望活久一些,更深入解讀樂譜,更少迷惘犯錯,發揮自己全部的技術及知識,更接近貝多芬及布魯克納不朽的音樂,即使只是一步也好。
最後,我附上與近衛先生晚年在我大阪愛樂休息室裡的談話。
我說:「得知先生出版了不起的新版本,不過最近這些年,我用原本的樣貌演奏貝多芬。」
近衛先生說:「那很好啊。我的版本是讓無能指揮家指揮差勁樂團也能演奏出色用的。」
這句話要如何聽取,包含了深厚的涵義。